 |
 |
毕飞宇讲《小说课》:我是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作家
发布时间:2017-03-15作者:审核:点击:
附件:
【财新网】(实习记者 杨泽毅)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推拿》作者毕飞宇自2013年受聘到南京大学担任教授,借此机会,他开始为渴望写作的年轻人分析蒲松龄、鲁迅、奈保尔等名家的小说作品。
毕飞宇有意识地避免学院派的讲课方法,从自己实际创作的角度出发,细致地解释每一篇作品为何能成为经典:“分析有多种式样,有美学的分析,有史学的分析,我所采取的是实践的分析,换句话说,我就是想告诉年轻人,人家是怎么做的,人家是如何把‘事件’或‘人物’提升到‘好小说’那个高度的。老实说,我做实践分析相对来说要顺手一些,毕竟写了那么多年了,有些东西是感同身受的。”
这段话作为他对教授工作的总结,记在了新书《小说课》的后记中。《小说课》辑录了毕飞宇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部分讲稿曾发表于《钟山》杂志,后广为流传,在网络上阅读量超千万。
2017年2月24日下午,毕飞宇携新书做客北京东四共享际,畅谈同时身为小说作者与读者的感受。

毕飞宇在新书发布会上
读书最大的好处是建立审美体系
毕飞宇乐于阅读与讨论小说,他称自己的名声在中国的作家圈里“有点臭”,因为只要一有机会和其他作家聊天,他就会缠着别人聊某一部作品、聊不完不让人家走,以至于被人说是“话唠”。
他将自己阅读小说的心态比喻为“玩手串”:因为是在玩而不是学,所以能一直持续很久也不厌烦,就像玩家将手串反复盘两三年。带着这样的玩心,他才能对一部喜欢的小说反复谈论,并用相对轻松的方式表达出来。
文学评论不是医术,不怕误判,这使他可以仅用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直觉去评价与分析作品。毕飞宇并不担心作者本人会对他的分析持有异议,文学研究的本质不是要得到作者的同意。在他创作的三十年历史中,也有学生将自己对他作品的研究论文发给他看,问他是否同意。但他总会回复:“亲爱的某某某先生或女士,你是写你的论文,你的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的,你没有这个义务。”
毕飞宇在《小说课》的一篇中写道:“如果那些论文只是证明‘毕飞宇这么写是因为毕飞宇确实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文学研究这件事就该移交到刑警大队,警察可以通过审讯作者来替代文学批评。”
事实上,正像他引用南帆的一句话所说:所谓经典,就是经得起课堂分析的作品。毕飞宇在南大课堂上的经历让他发现,每一部挑出来的经典小说,即便对于他这样一个无比挑剔的人也是完全经得起分析的。
将小说当手串“把玩”的次数多了,他与小说便互相浸润:“我个人认为,我所熟悉的小说,它上面是有我的体温的。反过来说,那个小说里面的许许多多的矿物质,也会到我的肌肤里面来。”
对于每一个人,一生中阅读过的所有作家和作品会慢慢在心目中建立起一个好小说的标准。“如果一个读者脑子里有一百部功夫小说的体量,他建立起来的肯定是功夫小说的标准;他如果脑子里面是一大堆的琼瑶,他最后也会成为第二个琼瑶。”
没有哪一位母亲能将自己的文学审美“生”给子女,人只能自行建立自己的标准。毕飞宇认为阅读最大的好处,就是帮助一个人建立美学标准,这会引领整个人用这个标准去写诗与写信、做事与做人,达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境界。
“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作家”
对于作家而言,写作就是向着心中的美学标准靠近的过程,作家的阅读历史由此与创作有着无法撇清的渊源。
毕飞宇自诩为“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作家”,因为他们这一代作家的生活经验没有40、50一代丰厚,无法单纯凭借生活阅历来支撑写作。虽然生活没有给他足够的素材,但毕飞宇通过阅读弥补了空缺,建立起自己创作的根基。
他在1975年左右“评水浒”的运动中得到了一部金圣叹的评点本,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水浒传》。在大学前,他反复翻看这本书,对金圣叹的评点印象深刻:
“我记得花和尚鲁智深坐在床上,有一个人去摸他,一个女人的身份摸他,一下子摸到鲁智深的肚脐。(金圣叹)一个括号补一个话‘意在肚皮之下也’。这个话像粗话一样,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话参与了小说创作。为什么?没有这句话我们(只)看到那个人摸了一下肚皮,这句话一出来,他刻画了摸肚皮那个人的心思。”
“比如有关潘金莲出轨之前的内心活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一共有十个步骤。在小说里边你是看不出来的,(写成了)一大段。金圣叹这个人非常坏,到了一个步骤的时候打一个括号,意思就是第一步,到第二部分的时候第二步,到第三部分的时候第三步,一直排下去,你就会看到——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的天啊,人心深似海是这么来的。其实施耐庵写得清清楚楚,(但)我不知道什么叫人心深似海,是金圣叹把人心深似海用阿拉伯数字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们。”
《水浒传》的文字教会了毕飞宇如何交待人物内心的全面和步骤。随着他后来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广,他看到了更多比《水浒传》在心理刻画上做得更好的作品,但是经典的影响力早已根植在他的写作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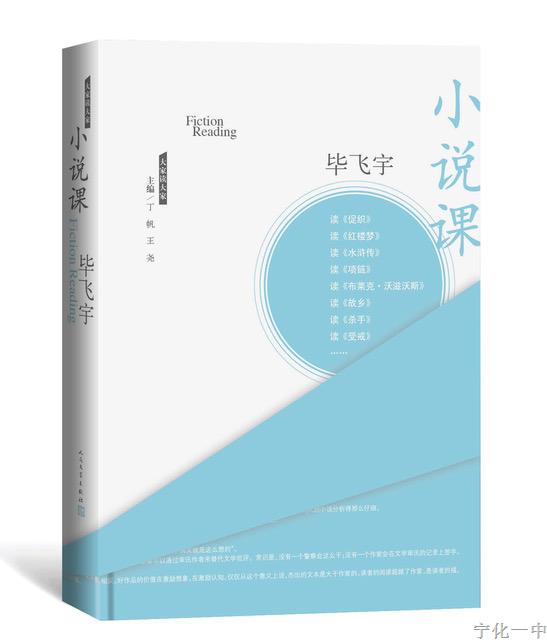
《小说课》
毕飞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01
感受与控制文字的温度
《小说课》中,毕飞宇在分析鲁迅的小说《故乡》时使用了一个概念:作家的基础体温。人总是对温度敏感的,不过从温度来谈文学并不多见。
他自我认知为一个偏热的人,而基础体温最高的作家也许是巴金:巴金“有赤子的心,有赤字的情……一辈子也没有降温”;基础体温最低的作家是张爱玲,她的冷能传到骨头缝里,“我要是遇见张爱玲,离他八丈远我就会向她鞠躬,这样我就不必和她握手了。我受不了她冰冷的手。”
另一个最冷的作家是鲁迅,这的确与大多数人对鲁迅的感受相同:尽管鲁迅小说中的故事往往是刚强、硬气的,但鲁迅的笔法却透出一股寒意。不过鲁迅的小说虽然冷,却又以他独特的幽默冲淡了冷意,使得文字不会过于有侵犯性。“如果说鲁迅先生没有他的幽默的话,他作品的文化价值不会打折扣,但是美学价值会打折扣。”
小说的“冷和热”并不是毕飞宇故弄玄虚自创的标准,而是与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理论、意大利电影新现实主义的长镜头拍摄一脉相承的。无论是作家还是导演,都会自觉地调整作品内部的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使人感觉不够亲切。导演会用十分钟的长镜头避免蒙太奇引致的情感剧烈升温,毕飞宇则是把语言的温度调控在一个适当的范围,让文章不要过于神经质。
更具体来说,文字的表面的温度与内部又是不同的。毕飞宇举例道,一个黑社会老大的辛辣并不体现在他表面的怒气和吼叫上,而恰恰表现在他对行恶的冷淡和沉稳上。字面上的温度并不等于故事内的力量,毕飞宇认同的“好作家”,无论在小说内部想要呈现出多大的力量、多么重口味的内容,首先都要保证文本层面的平衡与安宁。
凭直觉决定小说的走向
阅读小说时精密的分析不代表着写作时的照搬照做。毕飞宇在南大的讲座中反复向学生强调,他是为了把课讲清晰、让人能听懂,才分为一二三的层次讲解,现实中的作者绝不是对着技巧列表一条条写作的。
他将阅读与写作比为学打乒乓球:“你到体院去,老师们一定会给你看12个图片:第一个动作这样,然后这样,然后这样,一个弧圈动作做完了。那是老师在课堂上没办法,他必须让你对这个动作清晰,只能这么干。你说哪一个人打乒乓球的时候疯了,他神经病,把自己的动作像切黄瓜一样的切成那么多段?不可能的。”
教学时的条分缕析不能被误以为是写作的方法,在真实的创作过程中,毕飞宇的精神状态要更为混沌,更多的时候是凭直觉决定小说的走向。
很多人会问毕飞宇,在他写作长篇小说时是否会先写好大纲或故事脉络?他的答案始终是没有。一方面,他所处的60后一代作家本身就有着去故事化的倾向,比起之前的作家更不注重小说的故事性,因此故事的走向不是他的第一考虑。
另一方面,他在写作过程中也要满足自己的趣味。作家王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对一个作家而言,再没有比摆出一个故事大纲按部就班更索然无味的事情。
毕飞宇也难以忍受这种工作的无趣感:“我愿意永远没有大纲,我每天把电脑打开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是把昨天写的东西看一遍,然后今天我往哪走,临时做决定。当然这个决定有可能走岔了,没问题,我写了一个星期写岔了,我把这个星期写的东西全删了重新写。当我发现找对(方向)的时候,我的内心会充满喜悦的,那种喜悦比喝酒、比吃饭、比在足球场上打进一个球强烈得多。”
将临时做决定的权力完全留给自己,这是写作给予毕飞宇的自我奖励,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写作中找到乐趣。

资料图:毕飞宇
作者一定要写到最好才对得起读者
除了照顾作家本人的乐趣,作家在写作中是否会考虑到读者的喜好,也是毕飞宇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一个作家说他在写作的时候内心是装着读者的,你信这个话吗?其实是不可信的……你心里面装着一个读者,我要问你,那人是谁?那人是初中生还是博士生?那人是80岁还是26岁?那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在毕飞宇看来,所谓“作家考虑到的读者”,不过是作家本人。作家只能假设:如果这一段文字通过了自己的标准,也就能通过读者的标准。
因此,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水平而控制写作水准,从根本上就是荒谬的;存侥幸之心放松对写作的要求,也一定会被发现。毕飞宇说:“你一定不要以为这章小说都快结束了你滑过去就算了,人家可能注意不到。真的不是这样,好读者多得是,细心的读者多得是,有素养的读者多得是,懂小说的读者多得是。”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当对自己有要求,如果读者会比他更聪明,那么他一定要写到最好才对得起读者。而一位对自己有信心的作家应当知道,作品的生命可以超出自己的想象。毕飞宇用杜甫来举例,8世纪的杜甫在写作时大概想不到1300年后还会有人阅读他的诗篇,而这一千多年里,即便是与顶级的诗人杜甫相比,也一定有某些读者更加聪明、更能体会到杜诗里的妙趣。
很多年前在香港,一位年轻的学生读者曾当面举出他一篇不成熟的作品,指出了其中的一个问题。毕飞宇坐在台上,心中非常羞愧,但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他说:“你说的是对的,我不给自己做任何辩解,这个作品不好,你可以把它滑过去看我别的作品。”
现在的毕飞宇,在写好小说之后不会急于拿给读者,而是回过头放一放,等到一个问题都找不到了再去投稿。他会认真检验作品里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一直到对自己的作品看得恶心,再横下一条心发给编辑。
他认为,这样拿出来的作品即便达不到经典,也是作者足够负责的产品,是作者在这一阶段能力的最高体现。或许作者真的还没有达到自我的最高峰,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也不会回头去修改自己的作品,因为他作为作家的生命年轮已经在发表的作品里自然呈现出来:“你在19岁时候的作品,作品的每个字里面都有荷尔蒙的气息,你到了55岁的时候去改,你觉得那些荷尔蒙的气息很不体面,脏兮兮的,你把它全处理掉?不能的。19岁的作品充满荷尔蒙气息,你就让它保留荷尔蒙气息;28岁的作品当中有孩子尿布的味道,你就让它有孩子尿布的味道;35岁的时候小说里面到处都是咖啡的芬芳,你就保持咖啡的芬芳。你死了之后,你给文学留下非常完整的文学艺术的轨迹,它对文学是有用的。”

毕飞宇在发布会上介绍创作心得
认真对待笔下角色:人道主义的技术化
2014年,娄烨将毕飞宇的小说《推拿》搬上银幕,一举夺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与金马奖最佳剧情片。谈起电影版的《推拿》,毕飞宇用了三个字评价:特别好。
他曾对娄烨说:这个电影没有一个地方跟我的小说是像的,可是你看完电影以后却发现,小说里面的东西都在里头。娄烨对此非常高兴。
毕飞宇在写作《推拿》时,有意触碰了小说的大忌:没有主人公。在描写盲人这一极其弱势的群体时,毕飞宇坚持不愿意让作品中出现一位所谓的主人公,从而使其他人仅仅成为配角。小说是写人的,即使是在虚构世界里面的虚构人物,一个人就是一条命,对小说家来说,认真对待每个虚构人物,就和对待现实世界里的生命是一样的。他把自己的想法称为“人道主义的技术化”。
电影放映之后,作为线索串联起影片的“小马”黄轩受到了最多追捧,然而梁朝伟专门在柏林电影节上对黄轩表达了自己的惋惜:本来非常希望将评选影帝的票投给他,但是因为在影片中戏份太少,最终只能割爱。
等到台北参加金马奖时,娄烨终于告诉毕飞宇:“所有人都以为黄轩的戏是最多的,以为黄轩是男一号,我告诉你老毕,我在剪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专门算着剪的,每个人的时间几乎一样。”
这件事让毕飞宇特别高兴,调整每个演员所占的比例、每个角色在小说中的地位其实并不是难事,但是对于艺术创作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毕飞宇想体现出一个基本的理念:人一定是平等的,所以他在小说中避免厚此薄彼,而娄烨在拍摄电影中也尽力避免厚此薄彼。两人从来没有交流过自己的想法,却巧合地在艺术理念上达成了一致。
未来的写作计划
三年前,毕飞宇曾承诺在今年下半年拿出小说新作,然而他的创作状态被去年的一场大病打断。虽然现在这个作品已经写成40余万字,但由于自己的状态不如从前,他无法预测自己什么时候能写完。
不过他在文学分析上的工作还将继续下去。在创作之余,他还有两个目标:
“第一,挑一个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一部长篇,用十讲或者十五讲全部谈一个长篇,这个兴趣我是有的。
“第二,就小说的基本技术问题、小说美学的基础问题,比如说小说的叙事时间、小说的叙事空间、小说的节奏、小说的温度、小说的体量与容量等具体的技术问题,我想一章一章跟南京大学的同学们好好交流交流。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出一本这样的书。”

上一篇:这才是真正的高人(非常经典)
下一篇:少一份奢望∣多一份快乐